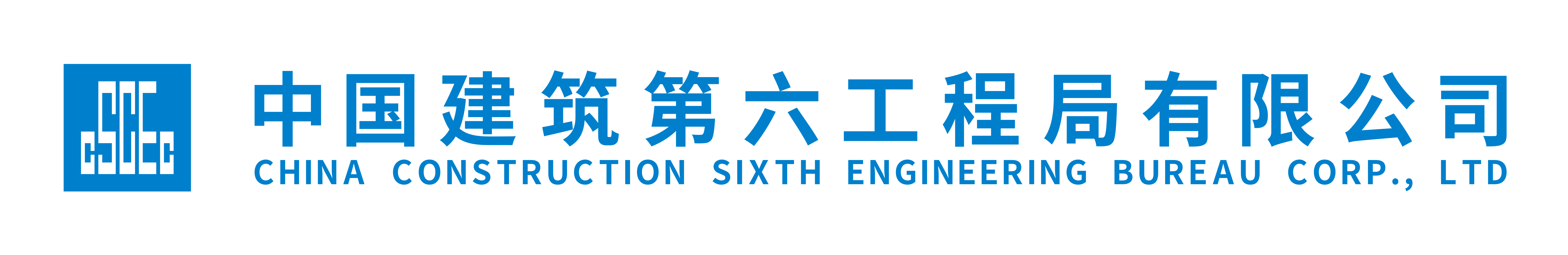中国古代文人有两种挥之不去的情结--仕与隐,仕与隐的矛盾一直与士人的人生理想和现实价值问题纠缠在一起,成为很多古贤人的痛苦,造就了独特的隐逸之风。
仕与隐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特别存在,从奴隶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,仿佛身上的胎记,终身不可磨灭。有官场的地方就有仕与隐的选择,仕时不忘归隐,隐时伺机出仕,求仕无果归隐;隐逸“独善其身”,出仕“兼济天下”。这似乎是多数古代文人的心声,这样的仕隐观的确称得上是一种情结。
不同的仕隐观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印记,更是折射不同的命运。陶渊明和孟浩然都是耳熟能详的与隐逸有关的诗人。陶渊明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现南山,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”一首诗道出了大诗人的归隐心境,但他却非池中物,一直隐于野。他,晋宋之际著名的文学家,仕宦家之后,一生五次出仕,末次县令之职在任仅80余天。“母老子幼,就养勤匮”迫他出仕;为了内心的自由,他选择“解印归田”,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和“性本爱丘山”是他隐逸的基石。他的隐逸,是捍卫自己人格尊严的正义之举,但更是对仕途失望后痛苦的抉择。孟浩然,盛唐时期有名的诗人,终生布衣,但穷其毕生为出仕。他起初隐居家乡,安慰自己内心说不想出仕,但出仕的小火苗一直在燃烧,到四十岁还想谋求一官半职,奈何最终小火只能湮灭,落寞归乡,终其一生隐居罢了。其实,隐逸之下谋求出仕,这不仅在盛唐时期流行,在其他时期也合乎仕人的思想。隐士代表人物除了陶、孟二人,还有李白、王维、白居易。李白的隐逸情结甚是复杂,一方面他确实想隐,可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隐逸不是长久的,隐隐出出,出出隐隐,到最后还是没能达到自己的目标。
古往今来,大凡隐逸之人的精神世界,必得到解脱,但这种解脱并不是每个隐士都向往的,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异常复杂的,除了解脱,还有不满、愤恨、痛苦和怀才不遇,或许掺杂着只为全身而退的心理,如“张良辞汉全身计,范蠡归湖远害机”,这些人大多是真隐。也有人隐为出仕, 怀抱“孔明心态”,三敦四请之后,便出仕;或怀抱“终南捷径”心态,虽然隐居于山野之中,却以隐扩大名声,伺机出仕。其实,若真想隐,心隐即可。
要想真正的隐逸,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所谓隐身先隐心,如果心里放不下,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深山中也无法真正过上隐逸的生活。浮华尘世,心净才能归隐,想真正的做到隐逸,首先必须使自己平衡,平衡内心的落差,平衡世俗的评价,了无牵挂,不受欲望驱使,人生方能真隐。当然世间也存在这样一种人,凡事都可以做到独善其身,对于这样的人,他所追求的隐逸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,其结果多半皈依自然,并且心中有“道”。
隐否?仕否?诸君选择,心若平静,居于高堂心静如水,心若嘈杂,隐于野市浮躁不安。(华东公司供稿)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