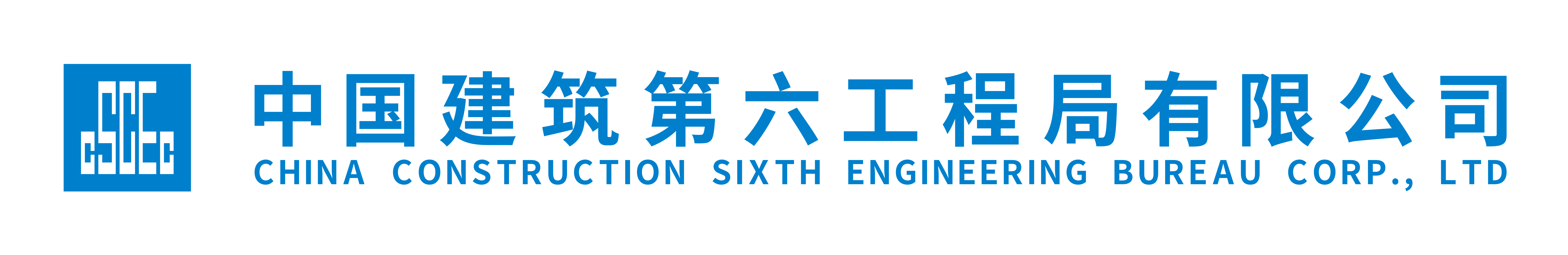季羡林说:“每个人都有个故乡,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。人人都爱自己的故乡的月亮。”——是的,不只是中秋,在每年的三百多个日子里我们都是那样地挚爱着自己故乡的月亮。月圆人亦圆,这才是圆满的中秋;月圆人未圆,所以才有了这无限的思念和感伤:月是故乡明。
说起来甚至有些悲怆:中秋过节的这个“闲儿”,大家却像往常一样一直忙到晚上六点半,直到夜幕降临,大家看到了丰盛的晚餐才算有了过节的味道。晚饭间,早已习惯了漂泊在外的老同志,免不了一顿高谈阔论和开怀畅饮;已结婚成家的年轻人,双双细细地相互夹着菜,也能享受半个家庭的团聚;今年才毕业的新员工,还未脱去稚嫩的学生气,羞涩着、腼腆着、排着队去挨桌儿敬酒……看到这些,我眼中竟有些亮晶晶的液体,不知道大伙儿家里的饭桌上,又有几双碗筷、几多欢笑、几分思念?我们在这里也只把思乡当是美味佳肴,一起吃下了。
长了二十八个年头,我也只是和父母过了十多个中秋,那都是十五岁之前的事情了,并且真正有记忆的更是那么寥寥的几个。后来上高中、上大学、从事工作,自此之后竟没有一个中秋是在家里度过的。想到这里,我忙在酒席间跑出来给父母和家人打了电话,电话也就只是潦草的几句:中秋怎么过的?吃饭了没?天冷记得加衣服,过年回不回家之类。这些千篇一律的话语却再次让我温暖了好久,是我自己不敢长聊,怕耽误了这边的酒席再没有了中秋的气氛,更怕聊深了思念的心就更不能自已。
是啊,故乡,有谁不喜欢故乡那缕清风?有谁不深爱着故乡的那轮圆月?又有谁在这样美好的夜里不思念故乡的亲人?我的故乡,那梁山,不青翠也是血气方刚的;那黄河,不秀丽也是气势磅礴的;而这里的我,虽不是七尺男儿却也是坚强执着的——漂泊的日子走了那么久,我们没有愧对自己的心中信念和肩上责任,因为这里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使命。
酒席散后,院子里是三三两两的人,大家手里都握着电话,说着不同的方言。我听不懂方言,但我听得懂大家的思念是相同的。有几个四五十岁的老同志给家里妻子、儿女打着电话,他们的年龄和我父母相仿,却也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分享着这轮寂寞的圆月,想起来不免多了几分敬畏、几分心酸。——这许多平凡的轮回,在我看来却是如此的伟大与美好,在平日,并非我们看不到,也并非我们不愿赞美,只因触动它便激起我们心中最深处的涟漪。
已是深夜,我在电脑前看到了几个同学还没有睡,彼此竟相互问起身在何方,问来问去,原来大家都没有回家,原来大家同是奋战在海角天涯。只是,问候之后便是无边的沉默,就如这夜色一样寂静。
“月是故乡明”,诗人的声音穿过千年的昼夜,千里的距离,让我在这中秋的夜里我做了长长的梦:梦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脸庞是如此亲切,窗前那片橘黄色的灯光,和故乡的明月一样皎洁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