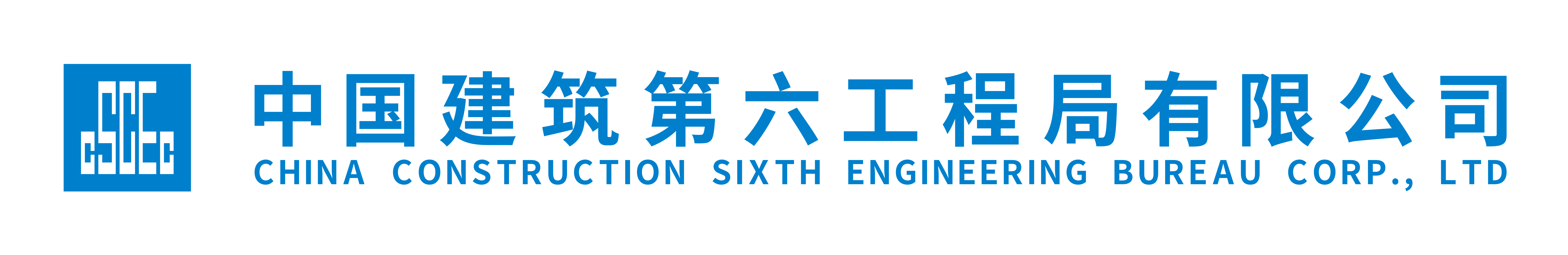维克多·雨果从小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。他曾经用自己的一生发誓,“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,要么一无所成。”然而若干年过去了,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。一百多年前,尼采“成为你自己”的呼声仍然在我们的耳际回旋,是的,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,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任何人,你的使命就是成为你自己——最好的自己。
学生们曾经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幸福,苏格拉底带领他们来到海边,让他们自己动手伐木造船,然后大家一同泛舟海上,清风徐来,悦目怡情,苏格拉底说,孩子们,这就是幸福!其实何止幸福,价值、意义、尊严、快乐……所有这些人类最美好的精神产品,都是自己动手创造的结果。要成为最好的自己,同样离不开自我意志的塑造。
存在主义认为,人性是开放的、是未定型的,人和动物相区别的地方在于,人没有固定的本质,人可以通过自我塑造创造出一个崭新的自己。黑格尔说,同样一句话,年幼无知的孩子与历经沧桑的老人说出来,完全不一样。没有经历和体悟,道理是生硬的、没有力量的。每个人的成长塑造都需要经历自己的奥德赛之旅。
《荷马史诗》记载,奥德赛在特洛伊战争中献出木马计,为战争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,但其居功自傲,得罪了海神波塞冬,被罚海上十余载的漂泊之旅。奥德赛凭着坚定的意志,战胜独眼巨人、食人族、海上女妖、地域恶魔等重重危险,终于和他的船员们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。
无悔的人生都应该有一场奥德赛之旅,只有历经岁月的磨合与历练,经历生活的颠簸与动荡,凭着坚强的意志,人才能找到自我、超越自我,并最终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,成为名副其实的自己。
生于“80后”的孩子时常感慨自己的不幸:“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,读大学不要钱;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,读小学不要钱;当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,工作是分配的;当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,却找不到工作;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,房子是分的;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,却买不起房子……”正如狄更斯所言,“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是最坏的时代。”但是就像我们不可能成为别人,时代也一样,没有谁可以回到已然逝去的时代,不管社会如何变化,我们都得生存,每天都得为稻粱谋,但是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你是如何利用业余时光的,是如何在觥筹交错、推杯换盏、呼朋引类、把酒言欢的诱惑下,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, “自私”地为自我塑造汲取阳光。克尔凯郭尔早就告诉我们,人群只不过是一堆噪音,一场幻象罢了。
斯蒂芬·茨威格在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这本书中说,“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,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,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”,乔布斯说,“你须寻得所爱。”一个人,在他的有生之年,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艰难困苦,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,却始终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,最喜欢做什么,最需要做什么,只能在迎来送往之间匆匆了此一生。
忘记曾经在哪里看到这样一尊雕塑:一个上身为人形、下身为石头的“半成人”用锤子和铆钉不断地雕琢、打磨着自己的身体,渐渐从石头里显露出一个完整的人形来。这个从石头里雕刻出自己的人,是一个名符其实的“自我塑造”之人。既然人没有既定的本质,人性也是开放的,那么自我塑造、自我成全也就成了我们终其一生的使命。因此,完全不必去羡慕那些“×二代”们,那些只追求过舒适安逸或温饱思淫欲之日子的人。靠父母赠与,靠美色换取,靠强取豪夺来的东西,与靠自己双手打造出的东西,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无悔的人生在于,由于我的存在,这个世界有了那么一点点不同,换句话说,我这一生并没有白过。毛泽东在其晚年轻描淡写地说,我顶多只改变了北京的几个大院。伟人如斯,我们自不必自惭形秽、妄自菲薄。美国农民诗人弗罗斯特有诗云:“他们望不了多深,他们也望不了多远,但谁能阻止,他们向沧海凝神。”的确,在这个水深波浪阔的时代,我们也许不能跟别人比翻云覆雨、弄潮逐浪的本事,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忘我地凝望沧海。
无悔的人生应该有一场奥德赛之旅,在一路的艰辛与奔波中自觉地塑造自己,努力使自己成为最好。在这个世界上,有的人坐轿子,有的人抬轿子。抬轿子的总是抱怨坐轿子的欺负他们,可他们却已经将抬轿子当成了一种习惯,从来没有考虑过为自己争取坐轿子的权利。人性的光辉,人格的伟大,总是极少数有觉悟的人来表率和捍卫。畜群是可怜的,又是可气的。就像沉醉于梦魇的人,即使他们看到了天光,听到了天籁之音,他们也会当成是耳旁风,继续呼呼大睡。离开自我塑造之意志,再好的条件也不能让人成为命运的主人。
|